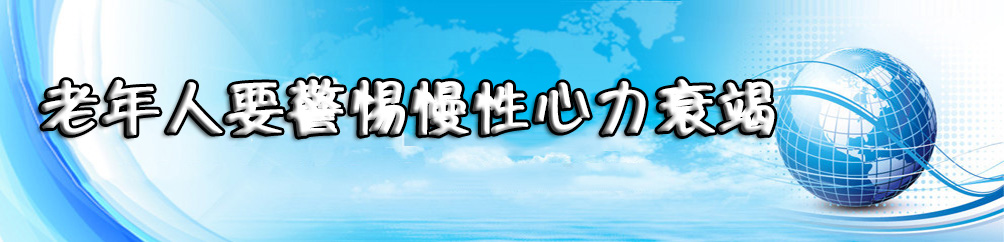
论著造影剂肾病对冠心病并发慢性心力衰
本文刊于:岭南心血管病杂志,,23(01):62-66
作者:卢旭升,许贤彬,杨平珍,林锐波,吴平彬
摘要
目的
探讨造影剂肾病(contrast-inducednephropathy,CIN)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并发慢性心力衰竭(心衰)患者临床预后的影响。
方法
自年1月至年12月,连续医院心内科接受经皮冠状动脉内支架植入术的冠心病并发慢性心衰的患者例,并进行1年随访。根据是否发生CIN分两组,比较其临床特点及1年随访病死率。
结果
例患者中,男例,女例,发生CIN32例(7.0%);CIN组中高龄患者(75岁)10例(31.6%),吸烟患者17例(55.1%),糖尿病患者17例(55.4%),急性心肌梗死伴休克患者5例(17.4%);CIN患者与非CIN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CIN组与非CIN组SYNTAX积分[(34.6±11.6)分vs.(21.6±7.8)分,P<0.01]、左心室射血分数(37.5%±9.87%vs.43.76%±3.45%,P<0.01)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CIN组在随访期间病死率显著高于非CIN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CIN是冠心病并发心衰患者1年死亡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CIN的发生与冠心病并发慢性心衰1年死亡风险显著相关。
我国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heartfailure,CHF)的患病率呈逐年攀升的趋势,其患病率已达0.9%。同时,CHF的病因在我国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风湿性心脏病发病率的减少,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oronaryheartdisease,CHD)已成为CHF的主要病因。作为CHF的主要治疗方法,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ercutaneouscoronaryintervention,PCI)治疗可显著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改善患者预后。尤其对于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PCI治疗已成为其首选的治疗方案[1]。因此,PCI治疗数量在我国逐年递增,作为其常见并发症之一的造影剂肾病(contrast-inducednephropathy,CIN)开始受到临床医生的普遍重视。据统计,CIN约占所有急性肾损伤病因的12%,是院内获得性急性肾损伤的第三大原因[2]。CIN的发生不仅延长了患者的住院时间,增加了医疗费用,也使得患者的病死率显著增加。既便如此,CIN与CHF预后间的关系仍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探讨是否CIN的发生可预测CHD并发CHF患者的1年死亡风险。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纳入标准:(1)年龄18岁,性别不限;(2)CHD并发CHF患者;(3)接受PCI治疗。排除标准:(1)CHF原因为心肌病、瓣膜病及先天性心脏病等;(2)疑似心肌缺血患者,仅接受冠状动脉造影而未行PCI治疗的患者;(3)肿瘤患者;(4)肝功能不全患者。
CHD诊断标准:在并发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基础上,患者出现静息下或运动时心绞痛,可被硝酸酯类药物缓解或不能缓解,心电图表现心肌缺血表现,超声心动图提示室壁运动异常,心肌损伤标志物等可升高或阴性表现,进一步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提示心外膜冠状动脉血管直径减少超过50%以上,即可诊断为CHD。CHF诊断标准:在CHD诊断基础上,患者出现静息或运动下呼吸困难、乏力以及水肿等临床症状,心动过速、呼吸急促、肺部啰音、颈静脉压力增高以及心腔扩大、心脏杂音等临床体征,实验室检查发现超声心动图异常、利钠钛(BNP/NT-proBNP)浓度升高等,即可诊断为CHF。
依据上述标准,自年1月至年12月,连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并接受PCI治疗的CHD并发CHF的患者共例。CHD并发CHF的诊断由2名心血管内科高级职称医师确定。反复住院患者以首次住院治疗情况为准。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研究方法
在我院心内科首次接诊时即获取并记录基本临床资料包括病史、危险因素、实验室检查及治疗情况。住院期间药物治疗均按相关指南给予标准化治疗。PCI治疗前记录患者的基线肾功能情况,PCI治疗后48~72h复查肾功能。入院48h内对患者行超声心动图检查。所有患者术前给予阿司匹林及氯吡咯雷各mg口服。PCI治疗中记录造影剂使用量、冠状动脉病变复杂程度(syntax积分)等情况。使用造影剂前4~12h至PCI治疗后12~24h给予0.9%氯化钠溶液连续静脉注射。根据患者心功能情况适当调整水化方案。CIN的诊断标准:在排除其他原因导致急性肾损伤的情况下,PCI治疗后48~72h血肌酐(serumcreatinine,Scr)较PCI治疗前增加44μmol/L或较基础水平增加25%[3]。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glomerularfiltrationrate,eGFR)根据我国年发布的公式计算:eGFR(mL/(min·1.73m2)=×(Scr,mg/dL)-1.×(年龄,岁)-0.×(男性=1,女性=0.79)[4]。出院后进行电话或门诊随访,记录患者死亡事件。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Kolmogorov-Smironov检验对计量资料分布进行正态性检验,若符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若非正态分布,则采用中位数(M)及范围(Q1~Q3)表示。计数资料采用频率/率表示。若符合正态分布,则两组间均数比较应用t检验,多组比较则应用方差分析。若不符合正态分布,则两组比较使用Mann-WhitneyU检验,多组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H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χ2检验。CIN与病死率间的关系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0.05被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上述所有统计学分析均使用SPSS19.0完成。
2结果
2.1两组临床特点比较
本研究共纳入接受PCI治疗的CHD并发CHF患者例。所有患者中男性占多数(69.6%),年龄(64.3±10.3)岁,LVEF为40.2%±16.8%,入院eGFR为72mL/(min·1.73m2),造影剂使用量(.5±20.5)ml,CIN的发生率为7.2%。根据是否发生CIN,将患者分为两组进行比较。两组N末端脑钠肽前体浓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ng/Lvs.(-)ng/L,P=0.]。两组年龄、吸烟、糖尿病、AMI伴休克、造影剂剂量、syntax积分、LVEF及eGFR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和表2。
2.2两组随访结果比较
所有患者随访1年,其中6例至少完成9个月后失访。其余患者在随访期间有21例发生死亡。与非CIN组比较,CIN组病死率显著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5.6%vs.3.7%,P0.)。
2.3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死亡危险因素分析
与非死亡组患者比较,CIN的发生率在死亡组患者中显著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利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校正SYNTAX积分、心率、左心室舒张末容积、纽约心脏协会心功能分级、院前血管紧张素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使用、eGFR及N末端脑钠肽前体后,CIN的发生仍与1年内死亡风险显著相关(P0.),详见表3。
3讨论
本研究发现,接受PCI治疗的CHD并发CHF患者中,与非CIN患者比较,CIN患者合并有更多的心血管病危险因素,且基线心功能和肾功能更差,这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心功能和肾功能受损分别是CIN的独立危险因素。随访1年结果显示,与非CIN患者相比,CIN患者病死率显著增加。进一步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CIN是CHD并发CHF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随着我国CHD患者患病率逐年上升,PCI治疗被越来越多的心脏专科医生及患者接受。然而,随着PCI治疗的广泛开展,CIN发生率随之显著上升,医院获得性急性肾损伤的重要病因之一。作为PCI治疗的严重并发症之一,CIN不但延长患者住院时间,增加患者医疗负担,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致死及致残率。因此,通过术前危险因素评估,早期预测对CIN的诊疗非常重要[5]。研究表明,一般人群中CIN的发生率为2%,但在AMI、肾移植、糖尿病以及潜在肾功能损害的患者中,CIN可显著升高。多数CIN为非少尿型急性肾衰竭,可表现为包括颗粒管型、小管上皮细胞、蛋白尿、尿酶升高、尿比重及渗透压下降等在内的尿检异常。在造影剂使用后需要连续监测患者Scr浓度变化以及时发现肾损伤。此外,肌酐清除率、尿肌酐、渗透压、白蛋白以及α1微球蛋白等也有助于早期发现CIN。
明确CIN危险因素是防治CIN的首要措施。早期评估并及时干预危险因素可显著减少CIN的发生。研究表明,肾功能不全、糖尿病是CIN的高危因素,CHF、原发性高血压(高血压)、脱水、组织缺氧、造影剂剂量过大等是CIN的中危因素;年龄、吸烟、高胆固醇血症以及非激素类抗炎药物可能为低危因素。重要的是,在上述危险因素中肾功能不全、糖尿病、高龄以及严重左心室收缩功能障碍等危险因素均同时与CHF患者预后密切相关。荟萃分析显示,CHF患者常常并发肾功能不全,其中肾功能恶化发生率在30%以上。肾功能恶化可显著增加CHF住院患者以及门诊患者的病死率,Scr浓度大幅度升高预示CHF患者不良预后。多项研究显示,与非糖尿病患者比较,糖尿病患者中CHF发生率显著升高,并且在CHF患者中普遍存在胰岛素抵抗以及糖代谢异常。Gilbert等研究表明,糖尿病和非糖尿病患者心力衰竭风险随年龄增加而增加,且糖尿病患者心力衰竭风险显著高于非糖尿病患者。DUABHYCAR研究表明,并发2型糖尿病的CHF患者1年病死率显著高于无糖尿病的患者。同时,作为一种严重危害患者健康的临床综合征,CHF不仅表现为心脏功能的下降,同时也常并发其他器官功能障碍。多个系统障碍的相互作用和制约,形成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继而影响CHF患者的预后转归[6]。与之前结果相一致,CIN患者中吸烟和糖尿病发生明显高于非糖尿病患者,提示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与CIN发生密切相关。既往研究已经证实,糖尿病是CIN发生的独立预测因子[7]。此外,与非CIN患者比较,CIN患者中冠状动脉病变更为弥漫和复杂,因此,可以解释CIN患者较非CIN患者使用了更多的造影剂,而大剂量造影剂的使用无疑增加了CIN发生的风险。SYNTAX积分作为冠脉病变有力的评价工具,已广泛应用于CHD患者的临床诊断、预后评价及治疗决策。有研究显示,CIN患者较非CIN患者有更高的SYNTAX积分,且可有效预测CIN的发生[8]。同时,在临床实际工作中,eGFR是术前评估CIN风险的主要工具[9]。与此相一致,本研究发现,CIN患者eGFR显著减小。此外,CIN患者的CHF更为严重,可能与长期慢性心肾之间的交互作用相关[10]。综上,CIN的发生可能是长期危险因素的累积作用以及多器官功能障碍交互作用的综合结果。
作为急性肾损伤中的一种,CIN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CHD并发CHF患者的预后。一方面,CIN可能与CHD并发CHF具有相同的危险因素暴漏。例如高血压、吸烟、糖尿病、高龄等不仅见于CHD并发CHF患者,也同样多发于肾脏病患者。研究表明,CIN和CHF中的共同危险因素如糖尿病、肾功能不全等可通过损伤内皮、凝血功能异常、微血管病变、心肌重构以及代谢异常等进一步恶化心脏结构和功能。当存在多种危险因素时,上述病理生理学改变则会产生叠加或倍增效应,尤其心、肾两个器官功能同时受损时。
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中CIN患者冠状动脉病变更为复杂,且死亡人群中,冠状动脉复杂病变患者比例也显著增高。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所有的患者均接受了最优药物治疗,但在糖尿病、肾功能受损患者中,完全血运重建率显著低于非糖尿病患者以及肾功能正常的患者。既往研究表明,CIN与冠状动脉病变直接可相互影响。冠状动脉病变弥漫可能提示存在严重的全身动脉粥样硬化,肾脏供血不足可促进CIN的发生。而CIN的发生可继发引起高血压、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氧化应激、血脂紊乱及炎症反应,这些因素又可以反过来加重动脉粥样硬化[11]。研究证实,在肾损伤的患者中,冠状动脉钙化及顺应性显著下降,这可能与肾功能受损后钙磷代谢相关[12]。
本研究随访结果表明,CIN患者死亡比例显著高于非CIN患者。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CIN是CHD并发CHF患者随访期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如上述,CIN使CHF预后恶化可能与多重危险因素的叠加或累及倍增效应有关。同时,心肾功能障碍的交互影响也参与其中。临床前研究表明,包括CIN在内的肾损伤可检测到大分子代谢毒素显著增加,继而导致全身微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状态,而后者已被证实与肾功能恶化及CHD病死率增加密切相关[10]。
总之,传统心血管疾病高危因素与CIN的发生密切相关,而CIN发生又反过来恶化CHD并发CHF的发展及预后。因此,早期识别并积极干预CIN危险因素对CIN的防治意义重大。积极管理并控制CIN和CHF的共同危险因素,优化治疗,减少造影剂用量和频次,以及尝试多靶点药物应用仍是今后临床工作和(或)研究的重点内容。
参考文献(略)